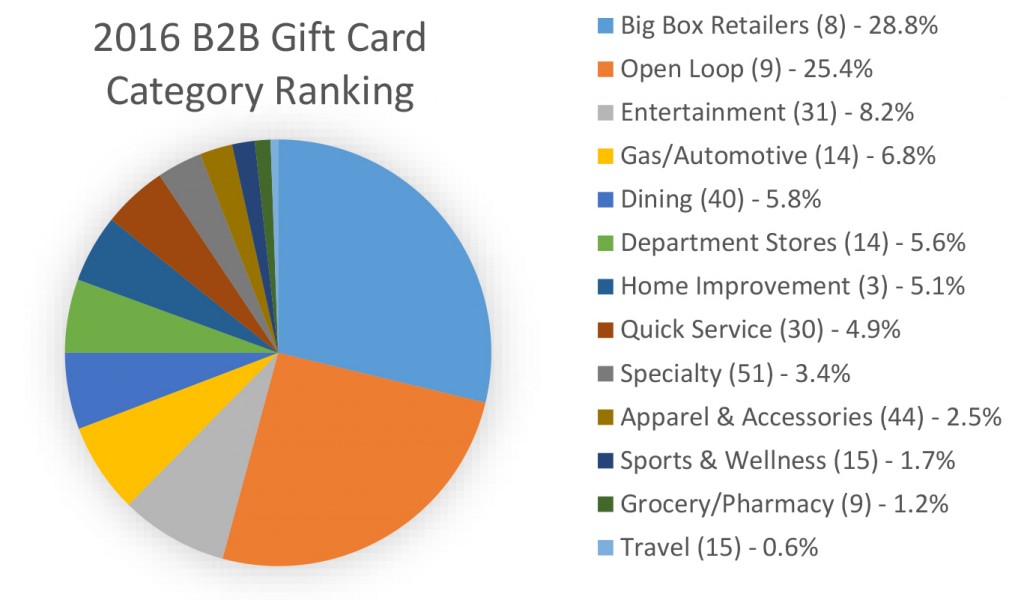扎根偏远乡村,她力图找到一种方式,帮助解决乡村教育的封闭问题——这是她的梦想
听上去如此雄心壮志,但这个在英国读完管理和金融两个硕士学位回国的北京姑娘,用11年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一个立志让社会变得更美好的普通年轻人,可以积聚多少能量
“其实我没想过实现一个梦想,得付出这么多代价。我的健康、青春、爱情……”璐瑶在夏日阳光中扬起脸,目光晶莹。讲起有一年,留学时的同学聚会,她因为忙着开营回不去,“大家都过得很好,但一个同学对我说,我好羡慕你,我们这么多人里,你是我知道的唯一在做自己喜欢的事的人。我说,我也觉得自己挺值得羡慕的。”
8月底,一场名为“非凡普通人——推动社会改变的力量”的摄影展在北京举行,展出照片全部来自担任过两届“荷赛”(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评委的摄影师王身敦。
过去5年,他用镜头记录了一群在中国各地长期从事公益事业、探索社会问题解决之道的普通人,赞叹他们“非凡”的生活方式,并想起日本作家盐见直纪的那句“一定有一种生活,可以不再被时间或金钱逼迫,回归人类本质;一定有一种人生,在做自己的同时,也能贡献社会。”
璐瑶是被记录的对象之一。从25岁到36岁,这个北京姑娘已经陪伴了一群乡村孩子11年。
扎根偏远乡村,她力图找到一种方式,帮助解决乡村教育的封闭问题——这是她的梦想。听上去如此雄心壮志,但她11年来的努力,足以让我们看到,一个立志让社会变得更美好的普通年轻人,可以积聚多少能量。
“乡村教育的根本问题不是贫困,是封闭”
2009年初,25岁的北京女孩璐瑶从英国读完管理和金融两个硕士学位回国,在正式踏入社会、当个小白领前,决定先到乡村支个教。
她报名参加团中央的西部计划,因为回国晚、报名迟,这年没招满支教大学生的地方只剩两个,一个在广西,一个在甘肃。
北方人嘛,觉得甘肃气候更好适应,她打电话问当地团委,“你们对志愿者有什么要求啊?”
接电话的人很幽默:“就三点,能吃土豆,会吃土豆,爱吃土豆。我们这边别的没有,就土豆多。”
她被逗得哈哈笑,改了主意去广西。
璐瑶不爱吃土豆,她有点挑食,爱干净,在别人眼里多少有点“娇气”。曾经14岁下乡插队的父亲总觉得女儿这代人打小在蜜罐里泡大,不知人间疾苦,也吃不了苦,她对此很不服气。
去农村支教,是璐瑶一直以来的愿望。
她对志愿服务有长久的关注,读大学时,每周末会去盲校做志愿者。但在人生的头25年,除了乡村旅游,她没接触过父亲口中那种“真正的农村”。
璐瑶要去支教的地方,在广西百色田阳县巴别乡,缺水、缺耕地、交通闭塞,当时的人均年收入不足1400元,她要教的学生90%是留守儿童。
春节后,给璐瑶送行,两个发小当着她的面打赌,一个赌她待不到3天就得逃回来,另一个赌7天。
但璐瑶想跑回北京的时刻只有在支教学校的头一晚。那天晚上,在自己枕头上看见一只拳头大小的红毛蜘蛛,她发出穿透宿舍的尖叫,引来一群孩子围观。
后来,她发现学校里还有许多其他小动物,为治老鼠她养了只猫,为治蜈蚣她养了只鸡。
英语课总上自习,或由其他科老师代课的孩子们有了一个北京来的英语老师。
第一节课,璐瑶给学生看家乡北京的照片,有孩子大声问:“老师,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平的?”
“我很震惊,生活在大山深处,他们甚至不能想象世界上有些地方是平的。”她思考支教半年能留下点什么,“我希望让他们对未来多一点想象。”
十年后,提起璐瑶的第一节课,好几个当年的孩子——阿国、“秘书”、苏童,都清楚记得,她教的第一个单词是“Dream”。她说,“以后可以不记得我是谁,不记得我教过什么知识,但请记得这个词。”
“她让我们猜它是什么意思,我们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来。最后她告诉我们,它的意思是梦想。第一次有人告诉我,这个东西很重要。”苏童说。
在巴别乡的每一天,璐瑶都有新的发现和感受,尤其当她开始家访,走遍全乡13个村子,她感觉,“每天都有东西咚咚咚地撞击你的心灵。”
去宝宝家,进门是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孩子。父母双双在外打工,十岁的男孩在长辈亲属帮助下独自生活。“家里谁砍柴?谁煮饭?谁扫地?”“我自己。”
在“秘书”家,问这个12岁的孩子梦想是什么,“我不知道梦想是什么。长大可以养猪、种玉米。”
艳艳发烧了,用手摸摸她的额头试温度,小姑娘突然就哭了,爸爸在外打工,妈妈离开了家,这样的触摸陌生而温暖……
纷杂的情绪在璐瑶心里积累,终于在一个清晨爆发。在那个起晚了的早上,她从宿舍出来,一眼看见一群孩子捧着饭缸、蹲在树下,埋头吃早饭。他们有的光着脚,有的穿着破旧的鞋,身上脏脏的。他们背后,是极美的青山白云蓝天。
“我脑海里一下闪现小时候常在北京看见的建筑工人蹲在工地门口扒盒饭的画面。”想到这可能就是这些孩子的未来,她眼泪唰地流下来。
这不公平。她想,凭什么?孩子生来有被陪伴,被爱的权利,未来该有无限可能。他们没做错任何事,他们的家庭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付出了。在村子里,老人没有子女,孩子没有父母,可他们没得到应得的。因为成长在贫穷乡村,他们缺少爱护、信息闭塞、教育资源和发展机会匮乏,对未来的可能性一无所知。
“过去,我认为乡村教育的根本问题就是贫困,是孩子上不起学、买不起书。但那时,我发觉比贫困更要命的是封闭。”
在封闭的世界,孩子没有足够的想象力谈论梦想。他们亲眼所见的人生道路,要么是像爷爷奶奶一样种地,要么是像父母一样打工。第三条路是学校老师讲给他们听的,要考大学,但他们并不清楚什么是大学,也不知道考上大学后做什么。
许多年后,璐瑶觉得,在那个莫名其妙哭到不能自已的清晨,冥冥中像有人告诉她:我们来做点什么打破这种封闭,如果这些孩子看不到未来的可能性,我们让他们看到。
这成了她的梦想,也让她的人生拐向另一个方向。
“我解决不了几百万人的问题,我解决几个行不行?”
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想帮贫困乡村的孩子们打破封闭,这可能吗?
最开始,璐瑶也没什么特别的办法。
在临近支教结束的一次家访路上,她跟同行的本地老师说,想发起一个助学项目,帮巴别的孩子联系一对一的长期捐助人。
那位老师的反应是:你能坚持多久?
他见多了来来往往的支教大学生、一时受触动说要捐钱的热心人,和许多为期一两年、效果微茫的助学行动。
“我被问懵了。”璐瑶说,“我说我不知道,但我愿尽最大努力,一直坚持下去。”
在当地老师协助下,她发起“巴别梦想家”项目。2009年7月,支教结束,璐瑶带着130多份走访来的巴别孩子资料回到北京,为他们寻找一对一捐助人。
她要求捐助人在所捐助孩子成年前的长达十年左右时间里,除了每月提供150-250元的助学金,还要与孩子保持联系,做其情感陪伴的伙伴和接触世界的窗口,决不能半途而废。
这种“陪伴成长”的要求,和她有限的“资源”,使得第一批得到捐助的孩子只有8个,捐助人全是璐瑶的亲戚,包括她的父亲、小姨、叔叔和婶婶。一年后,数字上升到31个。
回京后,璐瑶在北京金融街一家投行上班。在山里待久了,城市变得陌生,她觉得金融街的楼高得能叫人闪了脖子,走路时,几次撞上大厦透明的玻璃门。金融业是个闪耀着金钱光辉的行业,每天对着电脑,看财富的聚集和再分配,她总会想起巴别的孩子们,比较此地彼地,像做着一个没醒的梦。
整个人被撕裂,璐瑶觉得痛苦,“这明明才是我该走的路,可我难受。”
干了几个月,她放弃挣扎,辞职去一家公益组织,工资起码打了三折,但她得以学习怎么做公益项目,怎么更好地帮助乡村孩子。
日益感受到一对一助学不足以解决封闭问题,“信息来源单一,而且是虚拟的,孩子们只能听说,不能亲身体验。”2011年,璐瑶开始办参与式工作坊,组织夏令营、冬令营,请受助学生免费参加。
此后至今,每年寒暑假,“巴别梦想家”的孩子都会聚在一起“开营”,每场大营主题不重复,由璐瑶等组织者和孩子们共同设计,包括:与世界和解,走进社会、家、故乡和城市,认识我自己……
2020年夏令营,他们选定的主题是法律,“不做平庸之恶,实践智慧与善”,孩子们以破案侦探等身份,在游戏中学习法律知识,了解真实案例,培养公民意识。
只做室内活动还不够,“打破封闭,要走出去。”2013年起,璐瑶每年带几乎没离开过家乡的孩子们出去游学。第一回,他们去的南宁,孩子们逛了科技馆、动物园、广西大学,为了省钱,晚上6个人挤住一个标准间,但所有人都高兴得要命。
去城市游学参观也不够,她觉得打破封闭还得接触真实社会,2014年开始,“巴别梦想家”的孩子每年都要参加社会实践。第一次实践活动,是把他们带到百色市的公园,分成几个4人小组,每组给500元启动资金和6小时时间,比赛在城市里赚钱。
有小组卖花,有小组卖艺,有小组在公园门口以5块钱一个的价格买气球,然后站在卖家旁边尝试6块钱一个卖出去。
鼓起多少勇气,才敢跟陌生人搭话,碰了多少壁,甚至被当成骗子,委屈地大哭,最后还亏了本……“但这不就是真实的学习吗?”璐瑶说,有小组赚了13块钱,成员们高兴坏了,说是人生第一桶金。
在社会实践中,这群乡村孩子服务家乡的社区,体验城市的生活。他们亲历打工者的一天,去农贸市场分拣圣女果,去餐厅后厨帮忙;他们做乡村调研,给家乡拍纪录片,采访村里老人的故事……
转变悄然发生,有孩子发现:“我不再害怕新挑战,因为这些在‘巴别梦想家’早已尝试过。”
经过6年摸索,璐瑶总结出一套路径,她认为“巴别梦想家”通过创造一个社会化学习的实践共同体,探索着乡村教育封闭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们对社会化学习的定义是,把学习者浸泡在复杂、多元、真实的社会情境中,通过持续不断的体验和实践所发生的学习。”璐瑶说。
在长期举办的大量参与式活动里,他们一次次模拟一个乡村孩子从边缘到融入社会的过程,通过推动孩子在集体中的身份转变实现他们的学习、蜕变。
2012年,为赚取资金办工作坊,也为了扩展捐助人资源,璐瑶离开公益组织,进了上海一家上市公司。
工作强度大,她常来不及倒时差地到欧洲出差,还要去巴别带孩子们开营,但翻看她那两年的微博,不时会看到几句兴高采烈的“我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越来越清晰”“多累的时候看到巴别的照片都觉得如沐春风”“半夜做梦梦到‘巴别梦想家’茁壮成长,居然笑醒”。
2015年,纠结半年后,璐瑶不顾劝阻,辞职回广西,全心投入“巴别梦想家”项目。
这一年,璐瑶32岁。她说自己心里其实很害怕,但又怕再过几年,更没勇气,“对梦想的渴望能战胜恐惧和孤独。”
“有的事情,看到了没法装没看到。假如我从没去支教,我知道社会上有这种不公平的情况,但我也可以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可我确实看到了。我可以装傻,所有人都可以装傻,然后呢?社会是个共同体,乡村留守儿童有几百万人,他们最终都会进入社会。谁都想独善其身,但谁都没法真的独善其身。我解决不了几百万人的问题,我解决几个行不行?每个人都这样想,社会是不是就不一样了?”璐瑶说。
“教育的客体不是孩子,是环境”
璐瑶从没要求“巴别梦想家”的孩子学习多用功,考试考多少名,但从结果看,他们总带来惊喜。2015年,“梦想家”第一次有适龄参加高考的孩子,5人全部考入大学,阿国考上中央民族大学,成了巴别乡30年来首个考到北京读大学的考生。此后,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地质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几乎每年都有“梦想家”的孩子考到北京。
2016年,11个“梦想家”成员参加高考,全部考入大学,全乡仅有的两名考入全国重点大学的考生都在其中。
好消息每年都在继续。
加入“巴别梦想家”时,孩子们还是小学生,其中还有后来差点被学校劝退的“差生”,为什么他们都能考上大学?“就因为他们是自己想上,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见识过世界后,他们内生的动力被激发了,这些成绩不都是‘梦想家’的功劳,我们只是提供了一种学校和家庭之外的有所助力的环境。”璐瑶说。
她觉得每个孩子都是粒种子,给予阳光、水和土壤,都能发芽。
一定程度上,这些孩子打破了人们对留守儿童的刻板印象。在大学,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学校社团的领导者、活跃分子和班委,“当了各种部长,所以我们‘梦想家’理事会的微信群群名就叫‘神仙和各种部长’。”璐瑶说。
理事会是2016年“巴别梦想家”登记为“广西梦想家乡村贫困青少年关爱中心”,成为省级公益组织后,通过公开竞选选出来的,成员除了璐瑶,全是年满18周岁的“梦想家”孩子,他们参与所有决策,共同管理这个机构。
“所以,当人们说农村孩子到大学后会自卑,会不适应,没有责任感……这到底是孩子的问题还是环境的问题?教育的客体不是孩子,是环境,教育者要把劲使在环境上。”
提到“大环境如此”已成为一种方便的借口,璐瑶说:“我们忘了自身对大环境的责任,忘了每个人都是一个环境。”
近几年,早期加入“梦想家”、现在已考上大学的乡村青年们——他们被叫作“出栏梦想家”,纷纷在学习工作之余,回故乡服务更多乡村孩子,成为运营“巴别梦想家”项目的主力军。
这也成了“巴别梦想家”最独特的地方,给予其生命力。
曾经,璐瑶是个孤独的梦想家,在人生地不熟的田阳,带着迷茫独力支撑着这个前路未卜的机构。最初,她近乎奢侈地投入多年光阴,陪伴了不到100个乡村孩子。直到2017年,机构九成资金来自个人捐赠,她很难从基金会筹到款,人们质疑她的模式不成规模,效率低下,难以复制。
但现在,“梦想家”的孩子们回复了这些质疑。过去3年,几十个“出栏梦想家”动员了超过600名大学生志愿者,服务了约两万名乡村学生。像璐瑶做过的那样,他们发起、设计和组织工作坊,他们去乡镇学校办阅读活动,他们迁移服务乡村孩子的经验,为同样渴望打破封闭的乡村教师们做教师工作坊……“巴别梦想家”开始得到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2020年,他们在百色市教育局支持下,把夏令营从田阳县搬到百色市。
回顾过往,看着当年个头不及自己腰间的孩子长成可以依靠的臂膀,璐瑶觉得很奇妙。她想,自己是“巴别梦想家”从0到1的1,现在的“出栏梦想家”是从1到N的N,那N的N次方又会是什么样?
她有点佩服自己11年来的坚持,感激“梦想家”的孩子们在她无数个人生至暗时刻里带来的温暖。
当说好要一起回田阳办“梦想家”的同伴突然说“我不去了”;当免费提供服务,支持了近十年的孩子家长背地里说这些人最后肯定要骗钱,现在是还没到时候;当有人对单身的她指指点点,恶意揣测她的私生活;当有人不信世界上有做事不图钱的人,不肯看他们的第三方财务审计报告,就断言他们的财务一定有问题;当她从2018年开始给全职员工发工资,被质疑公益组织的人怎么能领工资……是孩子们的温暖支持她走到今天。
璐瑶永远忘不了2017年夏天,有伙伴离开,开营不顺利,她高烧不退,在筋疲力尽的夜晚,坐在办公室里嚎啕大哭,被“秘书”撞见。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当初的选择到底对不对,值不值?”她问。
“就算今天‘梦想家’关门了又怎么样?我的命运已经改变了。阿国、佑佑、亮,我们的命运都已经改变了,难道这还不够吗?”“秘书”说。
“那些更小的孩子们怎么办?”她又问。
一年后,2018年9月,“秘书”放弃在南宁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成为“巴别梦想家”在璐瑶之外的第一个全职员工。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老板我会在哪里?在做什么?也许像许多村里的小伙伴们一样,早已出去打工,甚至成为小混混了。所以我认为老板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然怎么会有今天的我们。”这个今年24岁,被“梦想家”的伙伴们取了绰号“秘书”,以至于一些小孩子忘记他的大名叫苏光富的年轻人说,他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想要承担更多责任,服务更多像自己一样的孩子。
“离开是为了回来”
今年8月,经由“巴别梦想家”理事长璐瑶提名与全体理事合议,苏光富被推选为第二任理事长。
在朋友圈里,璐瑶写道:“发起‘梦想家’是我做过的最牛的事情,直到我交出‘梦想家’。”
这种“交出”有过一回预演,去年冬天,在其他“梦想家”同伴帮助下,“秘书”首次在璐瑶不在场时,统筹了整场寒假大营。
2019年1月,璐瑶被诊断出肿瘤早期,住进医院做手术。她拿着病理报告单问医生手术能不能等过完寒假她办完工作坊再做,“命是你自己的。”医生说。
“你看,现在疤还在。”指着脖子上的疤痕,璐瑶爽朗地笑着讲起这段经历,在肿瘤医院的十几天,她每天晚上在熄灯后躲进厕所,通过视频远程跟进大营进展。顺利结营那天,视频电话里,她和“秘书”对着屏幕泣不成声。
今年理事会换届后,很少在别人面前掉泪的新任理事长发表完就职演讲,又一次对着前任理事长大哭,璐瑶说:“‘秘书’,谢谢你,没有你,我不知道现在的自己是什么样。”“秘书”说:“彼此彼此。”然后哭得更厉害了。
“走到今天,我们真的太不容易了。”璐瑶说,就从那一刻,她觉得自己11年前的梦想已经实现,孩子们打破了封闭,改变了命运,而且改变命运的孩子们回来了。
“离开是为了回来,为了那些在我们身后无法走出去的人们”,如今,这句话是“出栏梦想家”们共同的格言,被他们一再讲起,也通过各种方式付诸实践。
一位参与了今年法律夏令营的志愿者感叹:“在这些少年面前,不少大人可能都会被逼出心灵深处的一种‘小’来。”
璐瑶认为,这句话的精髓在于,这些来自乡村的年轻人不是只追求个人利益和阶层流动的“逃离者”,他们愿意为家庭、为家乡、为社会担责。
“巴别梦想家”像一个魔术箱,一群孩子进去了,出来了,改变了。11年中这个社群的哪些举措最有效?怎样让一些偶然成为必然?
“出栏梦想家”们正在研究这一课题,尝试从他们亲历的11年实践里提炼经验,创立可推广的理论模型,将之分享给全社会。
他们计划2021年通过展览等形式,向公众呈现研究成果,包括他们共同撰写的十年发展故事集、十年变化纪录片……他们期待为社会提供一种解决乡村教育封闭问题的方案,唤起更多人对乡村贫困青少年的关注。
有孩子跟璐瑶表达了做“巴别梦想家”全职工作人员的想法,“我希望‘梦想家’能成为一个好的工作机会,保证薪资待遇,提供成长机会,不要让大家觉得回来是种牺牲,这是我正在努力做的。”璐瑶说。
回想20岁的自己,她开玩笑说最初的梦想是“不劳而获”,每天吃吃喝喝、到处旅游,过悠闲的日子,可人生的际遇如此不可思议。
“其实我没想过实现一个梦想,得付出这么多代价。我的健康、青春、爱情……”璐瑶在夏日阳光中扬起脸,目光晶莹。讲起有一年,留学时的同学聚会,她因为忙着开营回不去,“大家都过得很好,但一个同学对我说,我好羡慕你,我们这么多人里,你是我知道的唯一在做自己喜欢的事的人。我说,我也觉得自己挺值得羡慕的。”
她跟父母讲,你们该为我骄傲啊。因为没照顾好身体,父亲至今都生她的气,母亲很心疼她。“这11年是值得的。”璐瑶说。
2009年去巴别乡支教时,她听人讲了个故事,说之前来的志愿者觉得这里太穷太苦了,就在学校门口的小黑板上写了一句“巴不得别离”。第二年来的志愿者,觉得这里风景美,人很淳朴,在黑板上加了一个“开”字,变成“巴不得别离开”。
轮到璐瑶的时候,她确实没离开,而是创办了“巴别梦想家”,“梦想家的意思有两个:一是每个孩子都是梦想家,二是它是孵化梦想的家。”(本报记者王京雪)
来源:新华网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有信息仅供参考,不做交易和服务的根据,如自行使用本网资料发生偏差,本站概不负责,亦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涉及到版权或其他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