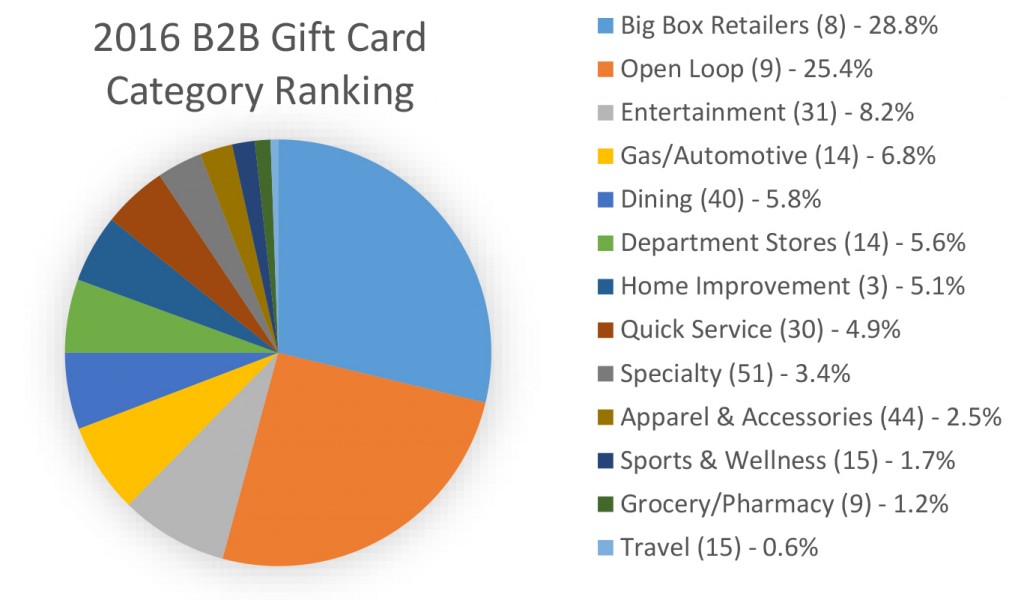卢琳能脱口而出这场高校“隐形资助”的种种细节,比如每条补助细则、整套受助者筛选标准,甚至是上回资助发放的日期。但一个关键信息除外:作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她在最初并不知道203名受助学生的姓名。但这恰是符合资助原则的。
今年9月开学后,在她工作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电”),“学校用大数据悄悄往困难生饭卡里打钱”的消息在网上铺天盖地,其实距离西电第一次向困难学生饭卡里打入720元补助已过去半年。
在河南省会的郑州大学(以下简称“郑大”),校园卡隐形资助10多年前已开始。期间也有院系辅导员提议,是否可向学生干部提供资助名单以便重点关注,但是提议因为“涉及受助学生隐私”始终没有通过。
“这些数据,其实一直都静静躺在学校信息中心的数据库里。”卢琳说。庞杂的校园大数据库在精准资助名义下才被激活。
大变局正在发生。今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6个扶贫日,也是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自2007年建立后的第13个年头。去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明了“精准资助”,并提出“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
不公示困难生认定名单、不用提交家庭贫困证明,一场保护困难生隐私和自尊的大数据隐形资助行动,在众多大学以各自的算法进行。
然而网络评论区对高校“大数据扶贫”的疑问也未曾停止:大数据真能筛出最精准的困难生吗?会不会有学生因为减肥、造假冒领等原因获得资助?每月100元上下的餐费补助对困难生的实际帮助大吗?
改变的起点
3元增量究竟能为大学食堂一餐饭带来什么改变?
这是西电大三学生黄旖收到校园卡资助后的一周,一直琢磨的问题。这笔720元补贴的资助标准是:一学期每天2餐,每餐补助3元。
在收到资助前,她的餐标是5元以内,在学校食堂几乎吃不上除了夹馍、鸡蛋饼等主食外一顿荤素搭配的正餐。但她谈及以前的餐食,没用过负面词汇,只说自己“爱吃,但更注重性价比”。
8元是补助后的餐标,不需多加节制就能在食堂窗口打到一荤两素。
收到隐形资助的学生浮出水面,大多因为善良“暴露”——卡里多了钱,他们最初以为是别的同学误充的,主动向辅导员澄清想要归还,黄旖也是如此。
9月25日19时黄旖去学校食堂吃饭,用餐高峰的人潮已散去。这个宿舍楼下的食堂是她最常光顾的,“大锅菜多,精品菜少,挺实惠”。
因为晚到,窗口菜少了,不少菜品被拼到一起售卖,菜也没了热气。黄旖不太在意,她仰头看价目表,盯了足足十几秒。
“这是没饭补前养成的习惯,很抠门儿,以前我会盯着价目表看更久。”黄旖说起以前她常会站在打饭的长队外犹豫许久,有时越看越急,索性拿塑料袋打个菜走了。
饭卡里每月多了180元后,她常去的是6元的套餐窗口,三素一荤的样式,口味差强人意,装餐食的是铝盘,不如8元套餐的白色餐盘精致。但这个窗口在用餐高峰时也会排起长队,黄旖在其中不再觉得自己另类。
校园有不少黄旖的禁区,比如校内两座商业综合楼大小不下百家餐馆,黄旖极少光顾。她还算熟悉的只有卖菠菜面的档口,小份西红柿鸡蛋面10元,面汤免费。她说有“在家吃饭的感觉”。但也不常去,她只在低血糖犯时才去那里改善一下。
再比如她常去的学校图书馆里有家咖啡店,饮料均价20元左右。黄旖2年多来从没进过这家咖啡店,她在记者“请客进去喝一杯”的倡议下第一次进入。落座后,她向四处张望许久,见有人在自习,她自言自语了句:“这儿那么吵,为啥不在图书馆自习区学呢?不划算!”
她现在最坦然的“奢侈一把”还是在食堂,偶尔点上一份10多元的石锅拌饭。
“学校食堂其实是人和人差距很小的地方了,我从大家的餐盘里看不出哪些人可能和我家境差不多。”一位坦承自己困难生身份的大二女生说。
公正的算法
如果肉眼看不出餐盘里的差距,那究竟什么可以?
西电信息网络技术中心的赵宇健老师在电脑里打开了“校园大数据决策支持平台”——答案就在这里。
要从大数据中淘出经济困难生,首先需要建立科学的量化指标。赵宇健把全校本科生2018年全年的消费数据调出,按早中晚3个消费时段把数据整合相加,获得了18.73万条数据。
结合学校平均水平,每月在食堂用餐60顿以上学生的消费数据是资助门槛之一,这是为了排除常叫外卖或外出实习的学生。
根据2018年西电学生消费水平统计,人均餐标是8元,学校把困难学生小额消费标准定在了5元及以下。“5元是一个临界点,因为我们发现餐标在5元区间的学生和在6—7元区间段相比,人数骤降。”卢琳说。
大数据最后筛选出每餐消费远低于平均水平的310名学生,比对学校困难生认定数据库,有144人在困难库,直接进入资助名单。
第二步就需要通过人工核实提升资助名单的精准度:学校通过深入学院、班级以及与辅导员实地探访的方式核实不在困难生认定库的166名同学,避免出现个别学生因为减肥消费较低等造成资助结果偏差。
人工智能学院辅导员杨坤当时就负责再审核,他趁集体活动时锁定目标,漫不经心地和学生聊起胃口如何、是不是因为吃得太少才身体瘦弱……经过验证,他学院里那两位不在困难生库里的低消费学生是因为“胃口太小”,他建议从初选名单中剔除。在这次人工复查中,166人中有59人被核实为困难生。
而郑大的校园卡隐形补助在精准度上探索了更久,比如校园卡资助周期是1个月,每月统计前1年的消费动态数据,选择1000名消费数据最低的学生进行资助,这样可即时增补家中境况突变导致生活拮据的学生,补助金额也按照困难程度分级。
郑大这份每月更新的大数据追踪还被应用在了辅助困难生认定,去年学校将此数据和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学生名单交叉对比,取消了部分有高消费行为学生的认定资格,同时增加了部分困难生入库。
“月更”结果是有效的。郑大小赵大二开学时收到过两三个月的隐形资助,那时正值父亲在工地上受伤,家中收入减少了大半。小赵本想每天吃馒头佐酱帮家里减负,但他那段时间的异常消费被大数据筛查了出来。
算法还在更新迭代中,比如在新学期资助开始前,两所大学都计划将学生校园卡绑定支付宝、云闪付产生的消费纳入统计。
家中度过困难期后,小赵的三餐消费恢复正常,补助也就自动停止了。此后小赵看到宿舍楼里有拎一袋馒头低头走路的同学,就会佯装轻松上前拍拍他肩膀问一句:兄弟,最近是咋了?凭借这种方法,小赵真的“捕捉”到一位家中遭遇困难的同学,借了300元钱给他。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理解这一切。”小赵用过来人的口气说。
对抗标签化
其实没有谁比黄旖更懂得“被公示”带来的困扰。
她上高中时,学校把困难生的资格公示张贴在大门口,“每个人的名字被放得很大”。第二天班里一个女生跑到黄旖跟前,拉着她的手问:“你真的是困难生吗,我怎么看不出呢?”当时黄旖没说话,苦笑一下走开了。
在学校倡议隐形资助后,闪现在卢琳头脑中的画面是:18年前她刚来西电求学时,同班一位女生在床沿喝稀饭吃馒头。冬天卢琳见她穿得单薄,特地从家里为她带来了一条毛裤,但那位女生谢绝了,理由是“不怕冷”。
而另一位家境贫寒的同学获得了一笔4000元学院里的企业助学金。此后她经常被指点议论,甚至有人说:“这就是拿了4000元的那个人!”
“现在资助体系完善了,困难学生面对资助的心态有所改善,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不在乎‘困难生’这个身份标签了。”卢琳说。
事实有迹可循,比如在西电上学期发放隐形资助的203名学生中,有59人是经过学院复查被发现的,原本不在困难学生库里。“说明有一小部分学生即使家境贫困,也不愿意主动让学校知晓。”卢琳说。
杨坤在一次暑期家访时意外发现,一位成绩拔尖学生家境很不理想,他询问学生为什么不申请助学贷款,回答是:害怕同学另眼相看。尽管再三疏导,这位同学在新学期依旧不愿提出困难生认定申请。
为了抚平困难生身份带来的焦虑,西电的助困活动常有很多“大费周章”的设计。比如有资助方为学校捐赠了几十辆自行车,学校在全校范围内举行了一次自行车慢骑比赛,在挑选参赛者时,除了吸纳部分普通学生更是通知了不少困难生。
比赛的结果是无论名次人人有奖。这样一场资助困难学生自行车的行动也就转化成了人人可参与的校内运动赛。无人机试飞、单反摄影技能培训,甚至是去外省参观访学,这些本意向困难生倾斜的活动都以全校活动形式开放,尽管在人选上还是会暗暗偏向困难生。
学校资助中心也听到议论觉得在助困活动中放入少数普通学生名额,是对困难生资源的侵占,但是老师们情愿背负压力,向学校争取更多参与名额。
不过也有的事需要“无为”。在西电每年出国交流的学生名额中,从不特设照顾困难生的名额,鼓励公平竞争。
在郑大,学校学生处处长刘超向记者说起过“提前设岗助学”的做法,也就是在经济困难的新生入学前,为他们设立勤工助学岗位,13年里受益学生已经有858名。“等到其他同学来校时,他们会展现出像学校主人的自信,家境带给他们的局促感就会消退。”刘超说。
黄旖也觉得进入大学后,自己对身份的焦虑在慢慢减退。
大一入学,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黄旖悄悄把表格掖在课本里,找个四下无人的时机拿出来写几句,现在写此类情况说明,她不需要躲闪了。
也偶有“隐痛”发作时,一次宿舍同学想要把所有打扫工具准备卧室和卫生间各一套,黄旖觉得浪费,有一套就够了,其他同学多有抱怨。黄旖一句话让气氛迅速降到冰点:“对,我穷!满意了吗?”
大部分时候,宿舍已有了默契,比如大家一块儿在微信群里约着出去吃饭,见黄旖过了许久没回复,就会主动换一家人均消费更低的餐厅。
直到现在,黄旖也说不上身边哪些人也是困难生,这个身份标签在这所大学正被刻意淡化。
何为公平
黄旖觉得自己也任性过——大二暑假,她参加了香港大学的暑期游学。
那年的游学项目有美国、新加坡等选择,香港的项目最便宜,加上学校补贴的游学经费,自费部分不超过2000元。即使如此,她还是犹豫了2天才告诉父母。
成行那周,大部分时间她都留在香港大学听课、吃食堂以节约成本。“我记得听专业报告时,全英文的有点难跟上,就尽量捕捉关键词。”听完高密度的英文报告后,回到宾馆是她的放松时刻,透过窗户可看到“维港一线海景”。
有一回,她在香港街头迷失了,手里拿着为朋友代购的东西。唯一为自己买的是杯网红奶茶,排了半小时队。
一年后暑假,一位拿助学金的高中校友找黄旖咨询香港游学事宜。可校友最终放弃了,因害怕被同学质疑“困难生资格”。
一位大学辅导员曾和记者说起,他学院一位女生的确因为“困难生报名参加美国游学”被指摘。刚听到那位女生要去美国,群情激愤,不少同学每晚定时在校内论坛“炮轰”她。而这位辅导员觉得有失公允之处在于,当时根本没人在意这位女生品学兼优,本就符合学校选拔的游学人选。
风声在新学年的困难生认定工作来临前愈演愈烈。他找那位女生谈话,女生特别希望和大家澄清。他请那位女生写下情况说明,打算在新学年学院困难生认定会上代她解释。
“我坚信这次美国之行对我太重要了,我也确信它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女孩在信里澄清了这次的自费支出,除去她勤工俭学以及奖学金积蓄,家庭负担的可能也不到1万元了,即使如此,她依旧自责不已。
那晚的认定会上,当大家听同行的学生说起女孩在当地只兑换了极少的美元,又说起她除了给亲朋买小纪念品没有任何消费时,全场沉默了。
“这就是他们真实存在的发展性需求,无论他们家境是否艰难。”郑大辅导员张晨曦说。
记者旁听过一场学院困难生认定工作会,会议一度陷入相同困境:一位申请人刚换了最新的苹果手机,同宿舍的人就手机是她自己买的还是亲戚送的讨论许久;还有位申请人喜欢手办玩具和电子产品,大家为他的爱好是否存在“过高消费”争论不下,后来证实他的手办不超过200元,而电子产品也是淘来的二手货才平息。
在郑大,一位接受过隐形资助的医学院女生让人印象深刻。她的着装简约却不失精心:微卷的长发、宽松的卫衣,丝毫没有生活拮据的烙印。女孩打趣说:“我擅长用最少的钱过上体面生活。”
当下大学,困难生该以什么面目出现?任何概括都有失公允。清晰的事实是:在这两所大学,收到隐形资助的还是困难生中的少部分。“我们隐形资助的学生人数,接近特困生人数,许多一般困难学生不在其中。”郑大学生处的魏东老师说。
“更多时候他们的缺口并不在3元饭补。”卢琳说起在西电每位同学每年可向学校申请2000元无息贷款,用于创新创业等发展性需求。
承认家境贫寒的学生需要更多发展的可能性,对他们的多元选择有更多认同,或许这只是公平的开始。
黄旖始终没对记者放下戒备心,反复确认隐私信息不会刊登,而且一直没向记者开放微信朋友圈。
“最好我的坦白能让和我处境相同的人拥有生活的勇气”,黄旖希望她是“暴露”在大数据算法密林之中的少数人,“一切都继续悄悄进行”。 (文中受助学生及困难生均为化名)(记者 杨书源)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有信息仅供参考,不做交易和服务的根据,如自行使用本网资料发生偏差,本站概不负责,亦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涉及到版权或其他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